1993年,黄家驹在日本摔伤去世,蔡澜前往为他操办葬礼,记者问蔡澜:“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,为什么愿意出手帮忙?” 蔡澜是香港“四大才子”之一,写美食、聊电影、品红酒,看起来和摇滚主唱没有一点关系。 可当黄家驹的遗体从日本运回香港,操办葬礼的重任,偏偏落在了他肩上。 “您和黄家驹非亲非故,为啥要插手?”记者举着录音笔追问。 蔡澜眯眼笑了:“我跟他不熟,但我知道,香港乐坛不能没有他。” 要说两人有多深的私交,其实没有。 1980年代末,Beyond在酒吧驻唱,蔡澜偶尔去听,点杯啤酒坐角落。 黄家驹唱完会跑过来敬酒:“蔡先生,我们的歌您觉得咋样?” 蔡澜总说:“有劲,像你们的人。” 后来Beyond红了,黄家驹在采访里提过:“蔡澜老师懂我们,他写的东西有血有肉。” 蔡澜则在自己的专栏里写:“家驹的歌,是给普通人打的强心针。” 黄家驹去世时,蔡澜正在写新书。 听到消息,他放下笔直奔机场:“我得去日本,不能让家驹的葬礼办得寒酸。” 为什么?因为黄家驹不只是歌手,他是香港精神的符号——草根出身,唱《海阔天空》鼓励打拼的年轻人,唱《光辉岁月》致敬曼德拉,唱《大地》关注农民工。 他的死,对香港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歌手,是失去一种“劲”。 “香港那时候乱,但家驹的歌让人觉得有希望。”蔡澜后来在节目里说,“他死了,这种‘劲’就少了一半,我得帮他保住最后的体面。” 蔡澜操办葬礼,不只是选场地、定流程。 他联系了所有能联系到的乐坛朋友,让Beyond的成员们不至于手忙脚乱。 他拒绝媒体过度消费,只让真正的歌迷进灵堂。 他甚至自己掏钱,给黄家驹的父母买了机票。 “家驹要是知道,肯定说‘别折腾’,但他值得这样的折腾。”蔡澜对记者说。 葬礼那天,记者又问:“您和黄家驹没血缘、没深交,图什么?” 蔡澜喝了口茶,慢悠悠说:“图个‘该’字。该帮的人不帮,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?” 后来有人翻旧账,说蔡澜和黄家驹“不过是一杯酒的交情”,蔡澜笑了:“一杯酒够啦,有些人喝一辈子酒,也喝不出真心。” “非亲非故”的帮忙,往往比“沾亲带故”更纯粹。 不图名、不图利,只图“该”字。 就像蔡澜说的:“这个世界,总有人得做‘该做的事’,哪怕没人记得。” 黄家驹的葬礼上,蔡澜没哭,但他在灵堂里站了很久。 后来有人问他:“后悔吗?”他摇头:“不后悔,我只是做了该做的。” 或许,这才是“非亲非故”的帮忙最动人的地方,不是因为有多熟,而是因为有多“该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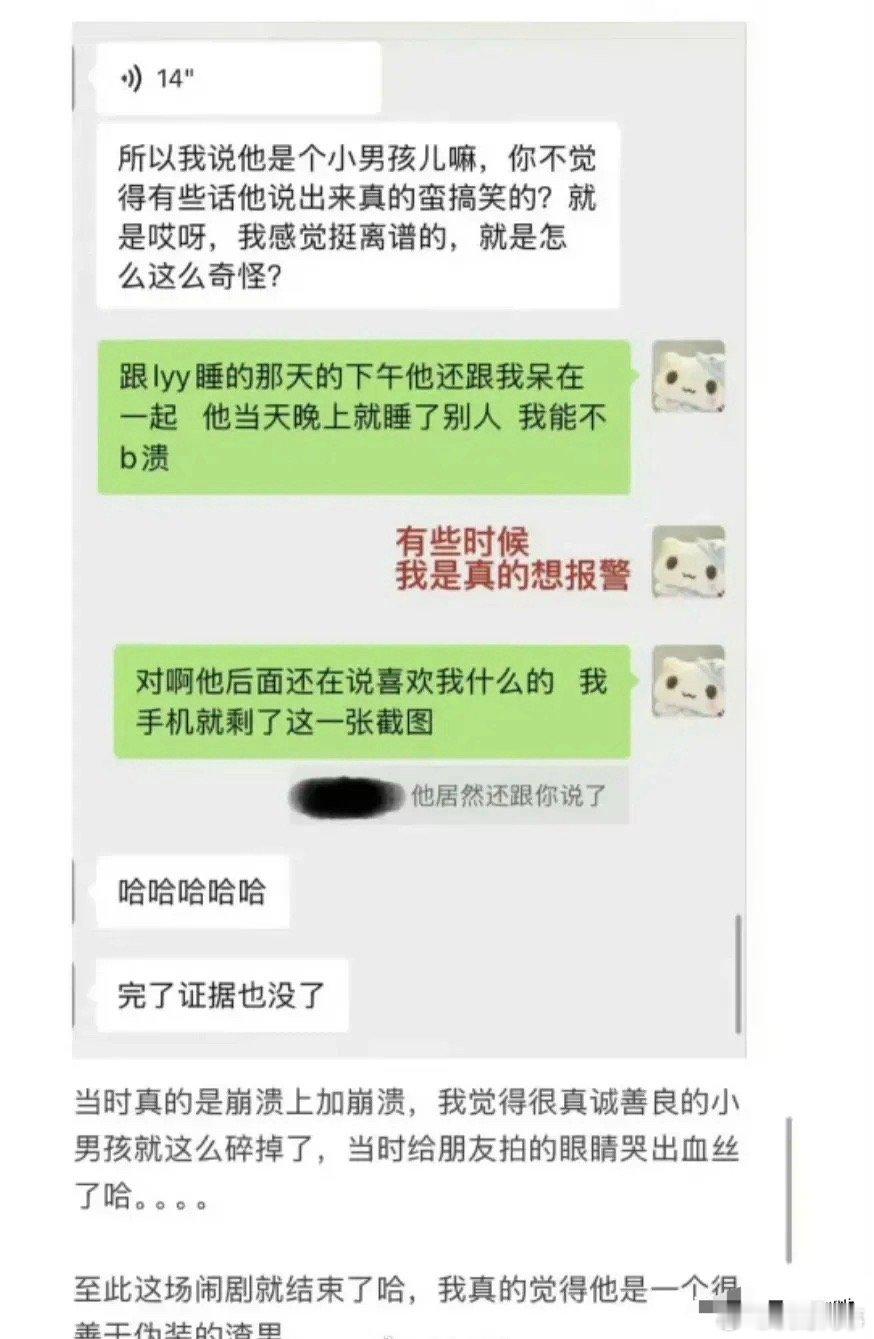


![王一博主演的电影《热烈》又又又获奖了[赞]。《热烈》依然热烈着,这就是好演员好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0975506234977416304.jpg?id=0)
![万茜:要不是拍戏我高低也得染个发[doge]夹在黄毛和紫毛中间小小一只[爱心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913597425017561116.jpg?id=0)
